江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民商法理論觀點,奠定了我國民商事法律制度的理論基礎;他躬耕教壇60余年,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被稱為中國政法大學“永遠的校長”;他一生堅信法治精神、并希望法治理念能夠得到普及,被譽為法學界的“良心”,他曾說:“我現在所能夠為社會做的還是吶喊……我盡量為中國現代應該有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做一些吶喊。吶喊總是能起到一些作用。”

2013年《出沒風波里:江平和他的時代》出版時,江平接受新京報書評周刊專訪。
季衛東在訪談中談到,江平先生豁達的人生態度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獨特的講演風格影響了一代代法律人,他敢于直言的勇氣、為弱者吶喊的擔當讓人敬佩,一生追求法治精神的堅定信念是后輩法律人的精神財富。

季衛東,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法與社會研究院院長。著有《法治秩序的建構》等。
豁達樂觀的精神
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
新京報:季老師,你和江平先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結識的?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你和他交往的過程?
季衛東:實際上我對江平先生的印象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當時他在中國政法大學推動法學教育改革,在政法大學的學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的一些朋友聽過他講課和講演,每次和我聊起來,都對江平老師富有感染力和思想深度的聲音印象深刻。遺憾的是,那個時候我沒有跟他直接見面。
我們正式相識是在1995年8月,當時日本東京召開了法社會學國際協會第三十一屆學術大會,我以指定委員的身份參加了主旨演講人的討論。江老師也是會議的主旨演講人之一,他長期從事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的研究和教學,在國際法學界非常有名望,很多歐美法學家都認識他。會議結束之后,我為他送行,有機會進行個別的交談,這是我們交往的起點。
后來在2003年,我當時任職的神戶大學舉辦了一場跨部門的大型國際研討會,我擔任這個研究項目基礎研究部門的負責人。我們邀請了相關領域的著名學者作為主旨演講嘉賓,例如經濟學家奧利弗·威廉姆森、人類學家安內利斯·瑞爾斯等,還有日本國內的民商法學界泰斗星野英一、北川善太郎。中國方面邀請的嘉賓則是江平先生,他與夫人同行。

2003年,季衛東與江平。
當時中國剛剛加入WTO,全球法成為學界熱點話題,中國民法典的編纂過程受到國外學界的高度重視。江平在會上作了相關主題的講演。國際研討會之后,我又邀請他到神戶大學對學生做一個關于中國民法典的主題演講。那一次我們進行了比較深度的交流,我和我的家人陪同江平先生和夫人前往奈良和神戶等地游覽。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聊了很多,他各種各樣的人生經歷,以及他的一些想法讓我非常感慨,這些后來都反映在2004年我寫的一篇文章《法不阿貴 方成公器》中,當時有一場慶祝江平70歲生日的研討活動。
2005年中國物權法草案頒布之后,我代表我的恩師之一北川善太郎先生邀請了國內日本民法學界的杰出專家參加關于中國民法典立法的論壇,出席活動的有崔建遠教授、王利明教授、房紹坤教授、王軼教授以及江平先生。當時的中國正在緊鑼密鼓地審議和修改物權法草案,圍繞物權法理的討論自然而然成為重點。
我回國任教之后,我和江平老師的交往就更加頻繁了,包括在各種研討會議場合上的見面。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我和同事在上海交大創辦一本《交大法學》的刊物,江平先生在得知后非常高興和支持,他為我們的新生刊物題寫刊名,并圍繞現代法治的精神與我做了一篇對談,作為卷首文章刊登在雜志的創刊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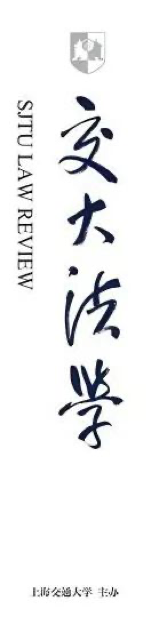
由江平題寫的“交大法學”刊名。
新京報:在和江平先生的交往過程中,他給你留下了什么樣的印象?
季衛東:首先給我的印象是豁達。他一生遭遇了那么多曲折和痛苦的經歷,但是一直非常樂觀,我們偶爾問起過去的事情,他也是一種云淡風輕的態度。你能感覺到,他發自內心有一種樂觀豁達的精神。
江平先生能夠堅持自己的信念,同時真正做到了說實話、說真話。尤其在一個社會發生巨變和轉型的過程中,這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
他的思想非常開放。上世紀50年代,江平先生被公派到前蘇聯留學,他接受的是蘇維埃式的法學教育。我在文章中提到過,他在留學歸來后,幾十年一直隨身攜帶著一本俄文版的《資產階級國家民商法》。可以說,他對西方一點不陌生,始終對現代法學主流有著清晰和深刻的認識。江平先生他們這一代學者很難得的一點是,能夠面對現實及時調整自己,彌補自己的知識結構上原有的缺陷,迅速適應和把握世界上發生的大事,這讓我印象深刻。
另外,江平先生講話時充滿了活力。他的聲音有磁性、透徹,很有感染力,能夠抓住任何一個聽眾的注意力,這可能與他原來在燕京大學修習新聞學有關系。無論是對學生還是對學者,無論是對中國學者還是對外國學者,江平先生在待人接物上都有一種很強的親和力。盡管我和他的接觸時間不是很長,我覺得我能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時刻感受到他散發出的人格魅力。

江平(左)在新京報2010年度好書致敬禮活動現場。
回到羅馬法傳統
抓住了中國法律秩序轉型綱領
新京報:江平被認為是中國民商法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參加了《民法通則》的制定,擔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組組長,是《民法典》編纂負責人,在《公司法》《合同法》《物權法》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就你的了解,江平在中國民商法的制定過程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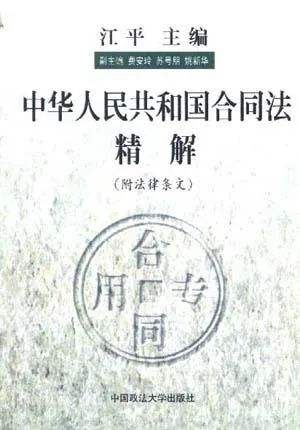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精解》,江平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3月。
季衛東:關于江老師在國內立法和具體制度改革方面的貢獻,我想有很多人比我更有發言權。我的專業研究方向是法社會學,法社會學和民法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因為它們關注的對象都是社會。我試圖從法律秩序構建的宏觀視角,談一談江平先生的學術貢獻。
我剛才也提到,江老師老一代人對于時代的變化和未來的發展趨勢有著敏銳的洞察力。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要從原來的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強調市場競爭、更有效率的市場競爭體制,這是當時中國的現實需求,這個轉型意味著思想的解放,也意味著法律范式需要有一場重大的變革。

2018年1月,法學家江平(右)與經濟學家吳敬璉(左)在新京報年度好書活動現場對談。
當時,江平先生迅速地意識到,我們的法律范式需要從原來的蘇維埃法律體系轉變為羅馬法體系,當時他在中國政法大學大力推動羅馬法的研究和翻譯工作,后來又主持世界法律文庫的編撰工作,我也受他之邀擔任編委。
中國法律的底子(包括民國時期)其實是大陸的成文法體系,蘇維埃法律體系也是大陸法系的一個分支。在法律制度的創新和移植的過程中,羅馬法作為現代法律的一個重要典范是繞不過去的,對于歐洲大陸法系來說尤其如此,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江平先生提出“回到羅馬法學的傳統”,對于我們國家的法律教育和法律解釋學的發展,以及民商法的治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抓住了法律秩序構建的綱領。
另外,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江平老師非常準確地把握了民法的本質。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民法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是社會改造的一張藍圖。比如,歐洲從原來的中世紀封建社會轉變為市民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需要對社會原有的身份關系和權利關系進行改造,民法重要的作用就是為這些從舊的身份關系中解放出來的個人提供自由的保障,給他們一整套的權利清單。我認為江平先生敏銳地抓住了民法的本質,也就是說要保護私權利、限制公權力,當然限制公權力不是盲目地限制公權,而是指以守法為前提,使法律上規定的個人權利能夠得到實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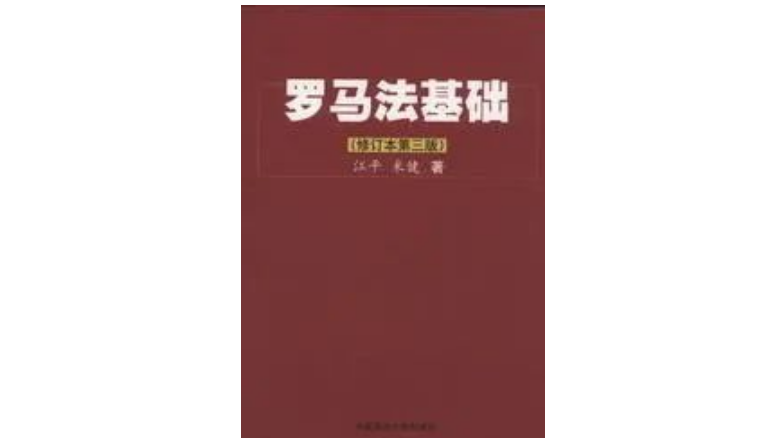
《羅馬法基礎》,江平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
無論回到羅馬法學傳統,還是深刻理解民法的本質,在這兩點上,能像江平先生這樣抓得這么準,說得這么透,用老百姓都能理解的語言,來說明一些非常深奧的道理,這在法學界也是非常罕見的。
此外,涉及具體的專業方面,比如江平先生擔任了《合同法》起草的主要負責人。中國在改革的過程中,原有的結構很難一下子改變,真正的變革是從合同關系開始的,這是真是非常重要的。從農村的承包合同責任制、城市國營企業改革的承包經營合同制、人事制度改革的合同工等,我們可以看到合同關系是中國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抓手。江平先生在整個《合同法》的整個起草過程中確實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這是在難得的歷史節點遇到了正確的人選。在這些具體的立法實踐中,江平先生非常精準到位地把握了立法精神,反映了中國的現實需求,也反映了整個世界演變的趨勢。
政法大學“永遠的校長”
新京報:江平在很多場合下說過,相比起法學家,他更愿意自稱為法律教育家,“以學校為舞臺,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現代法治觀念的,具有民主、自由開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學家。”你和他的學生交往頗多,是否可以談談學生口中的老師印象,以及江平在法律教育上被人忽視的貢獻?
季衛東:我有很多朋友同事都是江老師的學生。首先,他所有的學生對他都是發自內心地尊敬,對他的人格,對他的法治信念,對他的學識都非常欽佩。
我很遺憾沒有這個機會聽江老師的課,但是我聽過他的演講。江平老師的演講富有魅力,我發現后來很多中國法學界比較有公共影響力的法學家,實際上都受到了江平老師演講和說理風格的影響,包括現在的羅翔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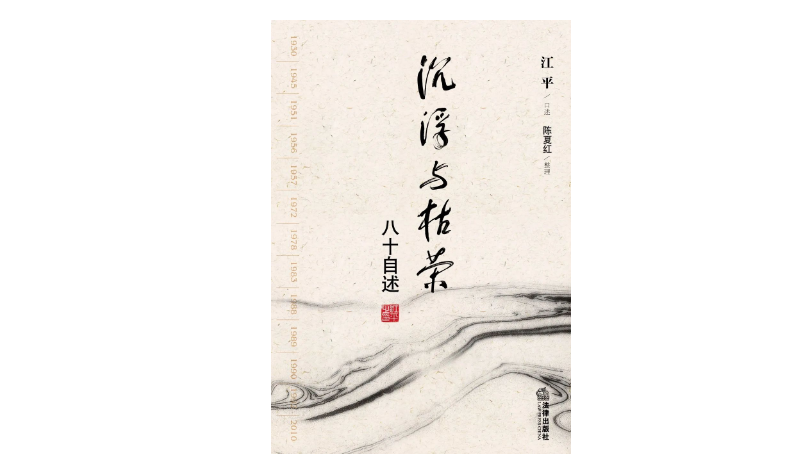
《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江平著,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
非常難得的是,江平老師身上有一種“有容乃大”的氣象,這在他的身上反映得非常明顯。江老師在各個領域培養了非常多的人才,包括學者、公共知識分子、政府官員、司法官員、律師等。江老師的學識很高,國際知名度也很高,在法學界享有非常高的聲望,但是他愿意接觸各行各業的人,愿意包容不同性情氣質的人。他能與一些自視清高的學者相談甚歡,也很樂意為一位普通律師的書籍寫序言。你可以在他交往的人群發現跨度極大的光譜。
江老師被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稱為“永遠的校長”,這絕不是沒有理由的。作為一所大學的校長,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真正領悟了大學的本質。他認識到,大學的靈魂在于創新,在于批判理性。他自身就具有這種批判理性,這是一種建設性的批判理性,不是盲目地破壞一切,而是真正建立理性的對話,在這個過程中尋求創新。他就是這樣教育他的學生,也是這樣鼓勵他的學生的。
參與的責任
新京報:江平先生不但親身參與了構建中國市場經濟游戲規則的立法進程,還始終以吶喊者的姿態,宣揚法治思想。理性、穩重、保守,通常是外界眼中法律人的形象,你怎么看待江平這樣一位在公共話題上沖鋒陷陣的斗士?這個話題引申出來的是,一位法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究竟有幾何?
季衛東: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當然也稍微有一點點難以回答。確實像你所說,一般來說法學家們口中的職業法律人,更強調的是制度、規范、秩序。他們注重治理的技藝,強調工具理性,用一種非常理性的方式來運作。
當然,法學培養的理念強調“legal skill”(法律技藝)和“legal mind”(法律精神),“legal mind”強調的是法律職業精神,這個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職業,不是我們常說的專才式培養。美國的法學院要求法學生讀過其他專業的本科再來讀法律,這背后強調的是一種普遍主義的培養方式。因為法律人不僅需要法律的技巧,也需要對正義感的把握,對外界事物認知的洞察力,只有擁有追求正義和公共善的情懷,才能在符合實際情況下做出理性公正的判斷,這也是法學教育注重博雅教育的原因。
此外,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強調律師這個職業的公益價值,這意味著律師這個職業具有公共性,需要有公共責任感和公共參與的意識。因此,法學家對職業法律人的理想形象應該包含這個層面,盡管在一般情況下是通過技術性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公共知識分子更多地關注公共問題,而不是僅僅某一個專業領域。公共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的啄木鳥,它能防止社會的病蟲害。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贊同把法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截然分開,他們對公共問題的關注是有共同點的。
盡管如此,法律人和公共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扮演不同的角色。現代歐洲把司法機構稱為“理性的殿堂”,這個隱喻反映出法律本身是強調理性的,它把社會中各種各樣互相矛盾的訴求,以及情緒化的因素轉變為理性化的技術問題。職業法律人更多地通過技術性方式處理各種矛盾,把所有激情的矛盾轉化為理性的處理,轉化到體制制度規范的軌道上,這是職業法律人的一個重要職責。如果說律師能夠發揮對公正的監督作用的話,它主要的體現為一種技術的監督。
但是在一個社會轉型的階段,律師有時候不免會訴諸輿論來改變自己談判地位的不利態勢,這時候就變得政治化和輿論化了。制度框架內的技術手段無法解決怎么辦?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人吶喊。制度框架內穩健的處理受阻的時候,這時一部分法學家就不得不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來改變它。在這樣一個時點上,江平老師自覺地擔當起了這樣的職責,扮演了這樣一種角色。法學家與公共知識分子合二為一的現象,在江平先生身上體現出來了。當然,我相信社會法治發展更進一步的時候,法學家還是更多地會考慮把社會的矛盾理性地轉化為程序問題、技術問題、規范問題來處理。
堅持法治的精神
是留給后人的遺產
新京報:提到法學家的素質,江平先生生前一直勸勉法律人要“知恥而后勇”。你對此曾作出過評論,陳夏紅撰寫的傳記《出沒風波里:江平和他的時代》中還專設一個章節叫做“季衛東之問”,顯然作者認為你的發問和江平老師的追求和理想有契合之處。我們如何理解江平先生所說職業法律人需要“知恥而后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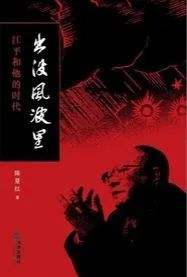
《出沒風波里:江平和他的時代》,陳夏紅著,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
季衛東:江平先生當年在向律師演講時提出“知恥而后勇”,在總結自己四十年執教生涯時對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也提到這個要求。這樣的告誡是針對當時司法腐敗、世風日下的現狀有感而發,因為有太多認識的同僚,他只是告誡大家要保留基本的底線。孔子說“有恥且格”,江平先生的“知恥而后勇”也是從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法律意識中尋找教化資源。
我聽了江平先生的發言后,有感而發,在之后的文章中提出一個問題:將來的史家以及人民會怎樣評判二十世紀后半葉的中國法律界的學術、實務以及人物?……在對良知進行交叉詢問之際,有些人可能要說我們“愧對江平”;也有些人則會慶幸有個守住正義底線的江老師,可以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減輕法律人的羞慚——這一點,從大家常說的“目前中國法學的精神脊梁”這句話上,已經可以略見端倪。
江老師的這句話到現在還是有意義的。江平先生談知恥,其實抓住了中國推行法治最關鍵的問題,這也是我們之前提到的法律職業精神,即法律人的公共善和正義的信念。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其實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法律人要守住底線,知恥而后勇,當然法律人應該還有更高的要求,但至少要守住底線。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你無法要求所有人都和江平先生一樣敢于說真話,但至少你不能說假話。所以我的文章標題叫“法不阿貴 方成公器”,如果你只是去迎合,你就失去了法律人的尊嚴和法律本身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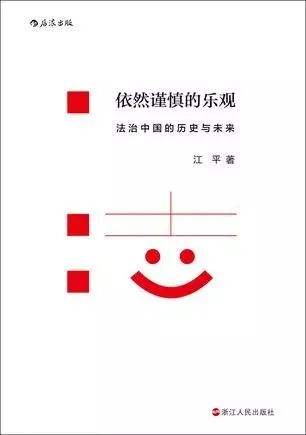
《依然謹慎的樂觀:法治中國的歷史與未來》,江平著,后浪·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
新京報:江平老師逝世之后,你是什么樣的感受?對法律人以及更廣大的普通人而言,你認為江平老師為我們留下了哪些精神遺產?
季衛東:在他去世前一天晚上,我得知他的狀況不是很好。后來經過搶救似乎情況有所好轉,但在最后還是(搶救沒有成功)。盡管之前多少有點預感,但得知消息后我還是非常悲痛,若有所失。
“世上已無江平”。以后這句話可能會經常出現,它的分量在于,江平老師代表的是中國法律人的良心,他為公眾尤其是弱小個體吶喊的精神,在特殊的語境中體現了法律人的職業理念、正義觀、公共善的追求。江平老師是中國非常稀缺的一種存在,接下來的問題是,他離去之后,這個空白由誰來填補?他曾經為很多人吶喊,反映了各種各樣弱勢群體的訴求,如今他在離開后,很多人在心中會留下非常大的空白,這種空虛和傷感是非常明顯的。
另外,江老師矢志不渝地堅持法治的信念。我之前談到,我對他的最初印象就是樂觀主義,他遭受那么多次挫折依然百折不撓,永遠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成為他不斷努力的精神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江平先生的離去以及他堅持法治的精神,可能對法學界是一次重新召喚。他告誡我們知恥而后勇,讓我們反思,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法治,什么才是真正的現代法治精神?江老師留下來的問題是需要我們后來人去回答的。
采寫/李永博
編輯/羅東
校對/劉軍












